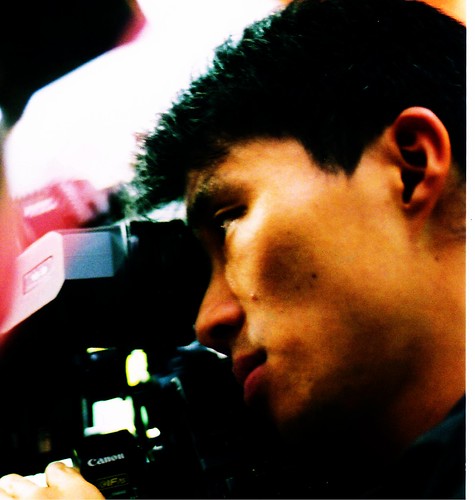成也蕭何敗也蕭何
大概是銅鑼灣吧,於軒尼詩道近波斯富街某處的高點,拍在百德新街電車站等上電車的梁家輝,穿插著幾個混合了懶有美感和神秘感的街景和/或電車的部份車身的鏡頭,上了車後坐在一個其貌不揚的少女旁(女主角徐乜乜),拿出考IQ的填格子數字遊戲冊出來,再發現對面坐著一位拿著報紙睡著了的糟老頭(另一個主角任達華),擠迫的車廂上乘客互相擦身而過,三個主角的眼光,都暴露在某個誰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場景中,任達華睡很昏了跌在地上,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他臭罵,有年青人拾起老頭跌下的報紙呆頭呆腦地看,所有人所有物所有場面設置都像意味著甚麼,像三個人在鬧市中打著曹達華時代峨眉派的「we wang wang」而整個城市的人都懞然不察,像有個不知誰人在不知甚麼地方一直把一切看在眼內,即是 eyes in the sky。
或者比不上《大事件》開場頭幾分鐘行雲流水直落冇cut的特大火力警匪巷戰,但《跟蹤》開場一幕,還是很點題地將片名所指的,用視覺技巧作了示範。開場的一連串鏡頭,先忍住不介紹人物關係各懷甚麼鬼胎,卻用剪接技巧把場境和氣份non-stop地綑了個邊,像上面一大漫無目的不啫邊際沒有句號的描述,然後你便會發現:這就是監視。
成也蕭何敗也蕭何,可能是對《跟蹤》可以下最中肯的評語。電影的結局帶著近乎宗教情懷的奇蹟,一輪鬥智鬥力後,任達華被梁家輝用小剪刀連插幾下,大動脈吧吧聲的流出一灘血泊以至任達華連笑話也說不完便昏倒,徐子珊在漫天風雨的街上失去了兇手的蹤影,絕望得跪倒地上雨水混和傷心欲絕的淚水。然後有了光,雨也停了,梁家輝的身影像偉人般從人群中冒起來,接著手瓜起展食野唔使比錢的警察如何能直搗匪巢重現眉目,連任達華也柳暗花明地醒來把未完的笑話說下去——嚴格地一個邪不能勝正的結果。
話說回來,就如上文所描述,電影的主題是作為一種行動的監視,既可以由全副裝備的警察進行,亦可以土炮地由梁家輝率領的匪幫演練。前者有用不完通街扮鬼扮馬的警力、針孔攝影機、偷聽器、取後八達通用戶資料和截聽的特權,後者則樸素地隨便挑一幢唐樓走到天台制高點看周圍環境,故亂報案記錄正要入蛇竇嘆茶的pc要多少時間趕到案發現場等等。換言之,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較技:匪幫做足功課就行動,看見附近周圍是線眼就call off;警察狗仔隊隨機應變死跟,鎖定了目標就開槍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,命運的economy是很規舉的。
雖然同是監視,這種純技術的較量,雖不比早排的《偷拍》般觸及人過往的歷史如何被偷拍監視行為引爆,但亦比《跟蹤》結果的道德主義宣判正邪來得清爽。事實上,警匪片如何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擺脫簡化的正邪二分,生哥的分析亦早已成為經典。沒有電影前大半段的克制和冷靜,不會對照出結局對於整個劇本的破壞力——天外飛仙得幾乎可當十分鐘的獨立短片看。沒有其他reference,難免叫人聯想是否因為要在國內上演或參展等理由。life is elsewhere,甚麼是電影的生命,哪裡才是電影的故土和別處,到底由誰來決定?